
4年辞职15次,95后「万辞王」来了
“97年的万辞王驾到。”这是徐畅在社交平台上的个人简介。
对于“万辞王”这个新生词汇,有网友如此解读:“干一行恨一行,行行都能干破防,不上班心发慌,上了班又只想躺。”
不是随便谁都有资格自称万辞王——4年前,徐畅从一所二本大学的中文系毕业。本科同学中,有人现在还在读博,而她已经换过15份工作,目前在找第16份。
她干过和专业沾点边的文案策划、活动策划和新媒体运营,也曾“脱下长衫”,做前台、当书店店员。她待过互联网大厂,也被招摇撞骗的老板忽悠进过创业团队。海量工作让她见识了“物种多样性”:画饼的面试官,摸鱼的店长,把开黄腔当有趣的男领导,以及她学不会的职场“宫斗”。
十一个月,是徐畅留在同一家公司的最长时间。风平浪静的话,大部分工作可以持续两到三个月。最短的一份,她只做了三天。
每次把辞职信甩给老板,她都觉得“太爽了”,平时厌烦的同事和办公室也变得“顺眼很多”。终于能从这个糟糕的环境逃走了,她想。
不过,一旦几个月没工作,虚无的感觉又涌上来,银行户头一点点变少的存款也催生着焦虑,于是她再度投简历,面试,带着痛苦面具上班,几个月后辞职。周而复始。
别人说她性格“冲”,这位万辞王承认。但自我怀疑也常常萦绕她:“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忍,就我一个人忍不了?”
带着困惑,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,没想到聚集了一大批万辞王。这些年轻的“王者”起码换过四五份工作,像她一样做过十几份的也不少。有人工作才三年,已经打过好几起劳动仲裁。
凤凰网和五位万辞王聊了聊。他们都是95后,学历和所学专业各不相同,但对于工作抱持着类似态度。和父母辈不同,他们不将工作视为人生意义的重要寄托,不信奉“劳动最光荣”的社会伦理,也没有“融入集体”的焦虑。
对他们来说,自己的感受最大。身边人常常评价他们“不稳定”“玻璃心”“缺乏忍耐力”,但在他们看来,是自己不愿向“有毒”的当代职场文化低头,尽管如是坚持需要付出代价。
于是他们以万辞王自嘲,一面消解现实生活带来的失落,一面昂起头为自己打气——如果一份工作里,要付出的劳动和情绪价值超过了能赚到的钱,“那就换一个”,徐畅说道。
01 职场小白的领悟:世界是个草台班子
2024年7月,徐畅正努力为简历填上新的一笔。两周前,一个行政岗位的面试现场,面试官问她,你有哪些技能?
她自信满满:Word、Excel、PPT、PS,我都精通。
面试官也侃侃而谈:我们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,优厚的年终奖和各种福利。
他们相视一笑。面试官和她握手:期待你的加入。
徐畅心里清楚,无论哪个办公软件,她都是“半吊子水平”。一定要说有什么擅长的,那就是搜索引擎用得不错——有什么不懂的,“万能”的网友都能解答。
她同样清楚,面试官在给她“画大饼”,但出于现实的压力,她只能接受,毕竟“活着更要紧”。
做过15份工作的她现在笃信,面试就是一场相互的“诈骗”。
她不担心“骗局”暴露,“有什么不会的,干着干着就会了”。
“从我换了N个工作的经验看,对于市面上百分之八十的工作,一个人只要智商没问题,干个半个月到一个月都能胜任,”徐畅说,“只要我能把工作做好,领导也不会计较我面试时有没有说真话。”
——毕竟,其他人的水平可能也差不多。刚工作时,她的学习劲头很足,遇到不懂的喜欢问领导,问资历深的同事。几次之后,她发现,“他们肚子里的东西也就那么多,也说不出个所以然”。
跳槽14次的郑雯对此也有着切身体会。她毕业于一所专科院校的动画设计专业,因为厌倦了一直从事的销售类岗位,决心转行计算机,零基础的她刷了两个月面试题,顺利入职一家互联网“小厂”。
刚进公司时,她战战兢兢,担心自己身为“小白”被嘲笑。不过她很快放下心来:公司里的其他同事,有的已经工作了十几年,有的名字前挂着高级职称,但技术水平还是“很水”——代码全靠搜索,搜索不到的靠“甩锅”。她恍然大悟,原来“大家都是混子”。
有人问她是怎么找到这么多工作的。她说,窍门就是自信,不要怕,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。
“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”,在凤凰网和几位万辞王的对话中高频出现。根据新京报书评周刊的解读,这句去年开始流行的网络用语,意在描摹一种“表面上光鲜亮丽,实际上各种问题漏洞百出,到处都有混子、投机者,认真、踏实做事的人没几个”的状态。
像是看透了世间真相一般,年轻的万辞王们决定坦然做自己——和在职场中放低姿态的父母辈不同,职场氛围的和谐、领导同事的认可,那算什么?既然职场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“打肿脸充胖子”,为什么还要假模假样地委屈自己?
于是,权力地位那一套在万辞王这儿不管用了——他们不愿、也学不会违心地对领导毕恭毕敬,笑脸相迎。
徐畅几次和上司正面“对线”。一次是在书店打工时,因为看不惯店长“什么都不做,还有脸来要求别人”,她激情澎湃地列举了对方的“十宗罪”并发到工作群,冲突以店长的主动辞职告终。不过这份工作也很快画上句号,因为在父母眼里,“终究不是正经班”。
还有一次是对着一个她认为“在外做舔狗,对内有点权力就上头”的老板。她带着写到凌晨三点的策划案向他汇报,他一眼没看,轻飘飘地来了一句,换个主题重写。徐畅拒绝,径自走出公司,结束了这份三天前刚入职的工作。
02“社畜模式”:奇葩公司全赶上了
万辞王不是一天练就的。他们也曾像其他打工人一样,渴望一份表面正常的工作。
二本毕业的陆帆自认对工作的要求不高,合法就行:朝九晚五,双休,收入四五千。但打开招聘软件,将地点定位到她的家乡,一座北方二线城市,几乎全是单休的工作,大小休的都很少。
更让她感到“炸裂”的是,当地很多公司不给员工缴五险一金。在她现在任职的一家外教机构,百来号员工里,没有一个上着社保,其中不乏干了两三年的人。
三年换过九份工作的陈晨有时觉得,怎么奇葩公司都让他赶上了。
他打过两次劳动仲裁。一次是他作为全职员工被转为外包,最后公司和他庭外和解。还有一次,他在无薪试岗一个月后被“恶意开除”,仲裁胜诉。
有一家公司在员工手册里明晃晃写着:上班期间听歌罚100块钱,闲聊罚300块钱,迟到一分钟扣50块钱,可累加,无上限。陈晨瞠目结舌:我是不是要倒贴钱上班?入职三天,他果断跑路。

陈晨的劳动仲裁现场
梁菲也打过15份工,在一年半之内。
干过行政,当过前台和服务员,也卖过鸭脖、鲜花、珠宝黄金、健身卡、二手房甚至是陵园墓地后,她得出结论:资本家一律把打工人当牛马使用。
在花店兼职时,她每天从早十点干到晚十点,这份工作突破了她对小时最低工资的预期,“你猜挣多少?6块钱一小时”。做服务员更累,每天中午上班,半夜下班,日薪100块。上岗不到一周,老板以“卫生不过关”为由扣了她三百块钱,她冲老板比了个中指,“直接走人了”。现在,她只想找一份工资和工作量匹配的工作。
“三千的工资让人干出三万的成绩,换谁都会跑路,”梁菲撇撇嘴,“每天当牛做马又挨叼,工资五位数还能咬咬牙劝自己忍忍,月薪三千忍不了一点。”
当“牛马”也就罢了,但今年23岁、做过12份工作(包括全职和兼职)的陆帆,不理解为什么同为牛马,还要争着“无底线内卷”。
那份工作是石膏头像手绘师。陆帆很喜欢这个职业,因为够“纯粹”——不用卖东西,不用跟人聊天,只要专心画像就够了。
入职第一天的中午,她放下笔,邀请同事一起去吃饭。同事摆摆手拒绝,从包里掏出一个面包,说要抓紧时间工作。她后来得知,这里大部分员工中午都不休息,吃个十分钟的便餐就接着画。而这般工作强度,获得的回报相当微薄:画一件石膏像,2元。如果客户退货,员工按照产品售价被扣工资,一次至少30元。
“我的天老爷,我觉得他们都是奇葩。”陆帆感慨。于是每天中午,她一个人到外面觅食,再散个步,晃荡够午休的一个半小时,再不紧不慢地回去。
同事私下和她说,自己也不想中午加班,但“大家都这样”,“不好意思不加”。
“可那是属于我的休息时间,”陆帆耸耸肩,“我就是觉得我不能被压榨。”
陈晨的“觉醒”一刻发生在无尽的加班之后。
那是一家规章制度写着每晚六点下班的公司,但陈晨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从没有早于晚上十点,凌晨也是常事。
每次深夜走出公司,他“还没有从社畜模式转换过来”,只觉得精神恍惚。直到下了地铁,走到小区门口,整个人像“泄了气的气球一样萎下来”,他几乎是飘着回到家,简单洗漱一下,一头栽到床上。
他试过和领导沟通。上司语重心长,“男孩子吃点苦怎么了,刚从学校出来就是要吃苦”。他懒得再争辩。
情绪在陈晨入职满月后的一个周末爆发。周六一整天,加班,周日白天,继续加班。到了周日傍晚,他把手头的工作收了个尾,去看早就买好票的演出。在剧院里,他的手机不停振动,是同事催他干活的电话和微信。他关了机。第二天,同事向老板告状,陈晨就坡下驴,递交了辞呈。
“我需要有自己的生活,享受一顿晚饭,和朋友聊聊天,看一场演出,不被打扰,”陈晨说,“我不想变成一个打工的机器。”
03 升级打怪,还是慢慢“学乖”
刚毕业时,徐畅也曾迫切地想在工作中学到点东西,想要大展一番宏图,幻想像《穿普拉达的女王》里的安妮海瑟薇一样在职场里升级打怪。但她很快发现,理想和现实之间隔着一道“马里亚纳海沟”。
徐畅曾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实习。四年多过去,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——
八点半,胸前挂着工牌的员工鱼贯进入公司。泡好咖啡,戴上护颈椎的套子,往工位上一坐,直到下班。喝水的频率不会太高,因为厕所的坑位有限。
在那里,同事间要以“XX同学”称呼,程式化的笑容是每个人的面具。足够客气,但没有“人气”。
在那里,她学会了一套全新的语言体系:赋能,对齐,颗粒度,感知度,心智,赛道……如何区分痛点、痒点和爽点?中文系毕业的她对着字典研究了许久。
在那里,沟通要“留痕”,因此交流大多发生在线上。办公室里,人声不常有——相邻工位的同事可能一整天说不上一句话。更多是密集的“哒哒哒”打字声,以及频繁响起的“叮”,那是办公软件的提示音。
在那里,时间精确到分钟,万事都要预约,即使是和相隔十米的同事沟通一个简单的问题,也要在办公软件上问,五分钟后我们去会议室聊?
最恐怖的事无外乎绩效被打低分,她听说不少同事在绩效考核前会彻夜失眠。
“每个人都像是被一个职场的壳子套住了。”徐畅觉得压抑。三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,她再没考虑过进入大厂。
从学校步入社会,徐畅逐渐发现,许多过去的行事法则不再适用。
比如对于高效率的追求。第一份工作时,老板叫她写一份项目书,她干劲满满,“肝”了个通宵,第二天早上就把打印好的文稿放到了老板办公桌上,心里还颇有些自得——在学校时,“快手”的她总是老师表扬、同学羡慕的对象。
期待的称赞没有出现。老板拿着项目书端详了一会儿,语气微妙,“写得真快啊......你今天也别闲着,把XX项目的策划做了”。她分明记得那是一个已经“流产”的项目。
走出老板办公室,她满腹疑惑,问同事什么情况,对方语气冷淡,“我在忙”。直到听到同事跟别人抱怨,“小徐怎么这么卷”,她才意识到自己“犯了傻”。
从那之后,她“学乖”了。DDL(截止日期)是哪天,她就哪天交。老板和同事对她重新展露笑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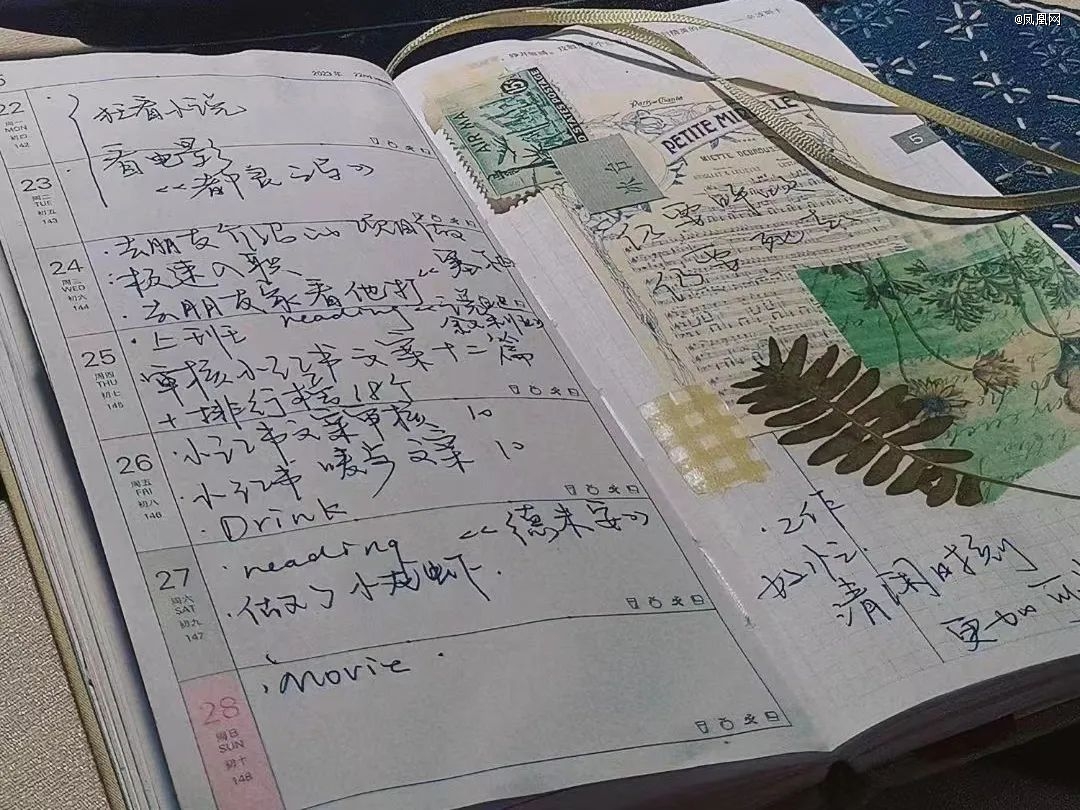
徐畅的工作计划
但还有一些做法和规则,是徐畅至今无法理解和适应的——
比如,一整天都没有工作,临到下班点又被安排开会。比如,领导一句不满意,整个项目组就要通宵改方案。比如,员工下了班不能走,不是因为还有工作要做,只是因为领导还没走。还有那些“屎上雕花”的工作,“没实质意义,纯粹为了好看,为了做面子”。
有一次,她负责策划一份文案,老板反复叫她修改。这次说这句话应该放在前面,那句后面不能用逗号,下一次又说,还是应该把这句放后面,标点换回逗号比较好。
这样来回改了十几遍之后,她“火”了,直接冲老板说,我真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在这些细小的地方一直纠结,这句话放在前面和放在后面,意思有什么区别吗?她追问,既然你要改,你告诉我,到底怎么改?这样改的意义是什么?你真的觉得这样改会更好吗?
老板哑口无言。后来,她逐渐被边缘化,工作清闲,但没意思。很快她主动请辞,一如既往,“何必等到最后你把我开了,我自己先走算了”。

新媒体运营人的日常:拥有许多只手机
除了职场对打工者无差别的虐,身为女性,徐畅还在公司遭遇了性别不平等,甚至是言语暴力。
她曾在一家个护品牌工作。一次脑暴会上,徐畅和同事讨论公司产品在公共厕所的广告投放策略。隔壁部门一个男性小领导突然插话,不如在男厕所贴上AV的视频链接?在坐着二十多人的会议室里,他甚至学起了AV里的声音。在场的男性哄笑。
徐畅浑身狠狠一抖,转过身怒视拟音者:你有毛病吧,低不低俗?
对方全然不在乎,继续嘻嘻哈哈:对啊,我就是这样一个低俗的人。
被徐畅骂过几次后,那个男领导不敢再在她面前开黄腔,但继续骚扰其他女同事。她们不敢声张,只能一脸苦恼地找到徐畅,请她帮忙,“去说说他,这个人真的是脑子有问题”。
同为打工人,徐畅和身边人的感触常常是相通的。领导是傻X,同事是傻X,公司在做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项目,业务领导明明什么都不懂,还要求我们做这做那……她经常在他们口中听到类似吐槽。
但万辞王和普通人的最大区别是——“我为什么要忍?”
04 “死刑犯”,在忍和不忍之间
离职一时畅快,作为万辞王,却不得不承受长久的代价。
最直接的是下一次求职时面试官的“拷问”。每次因为“不稳定”被judge,陈晨都在心里大喊,“你以为我不想稳定吗,我比你更想我稳定”。
无奈之下,万辞王们被逼成了一个个“简历裁缝”,在每次面试前努力“缝缝补补”:只留下那些在职时间长、和岗位相关度高的工作经历,“反正短的不交社保,即使做背调也查不出什么”。
但大段的职业空白期同样会引起面试官的质疑。对此,他们也逐渐掌握了应对的话术:“没工作的时候,我在尝试做自媒体,也会接一些散活儿”——要诀是,别闲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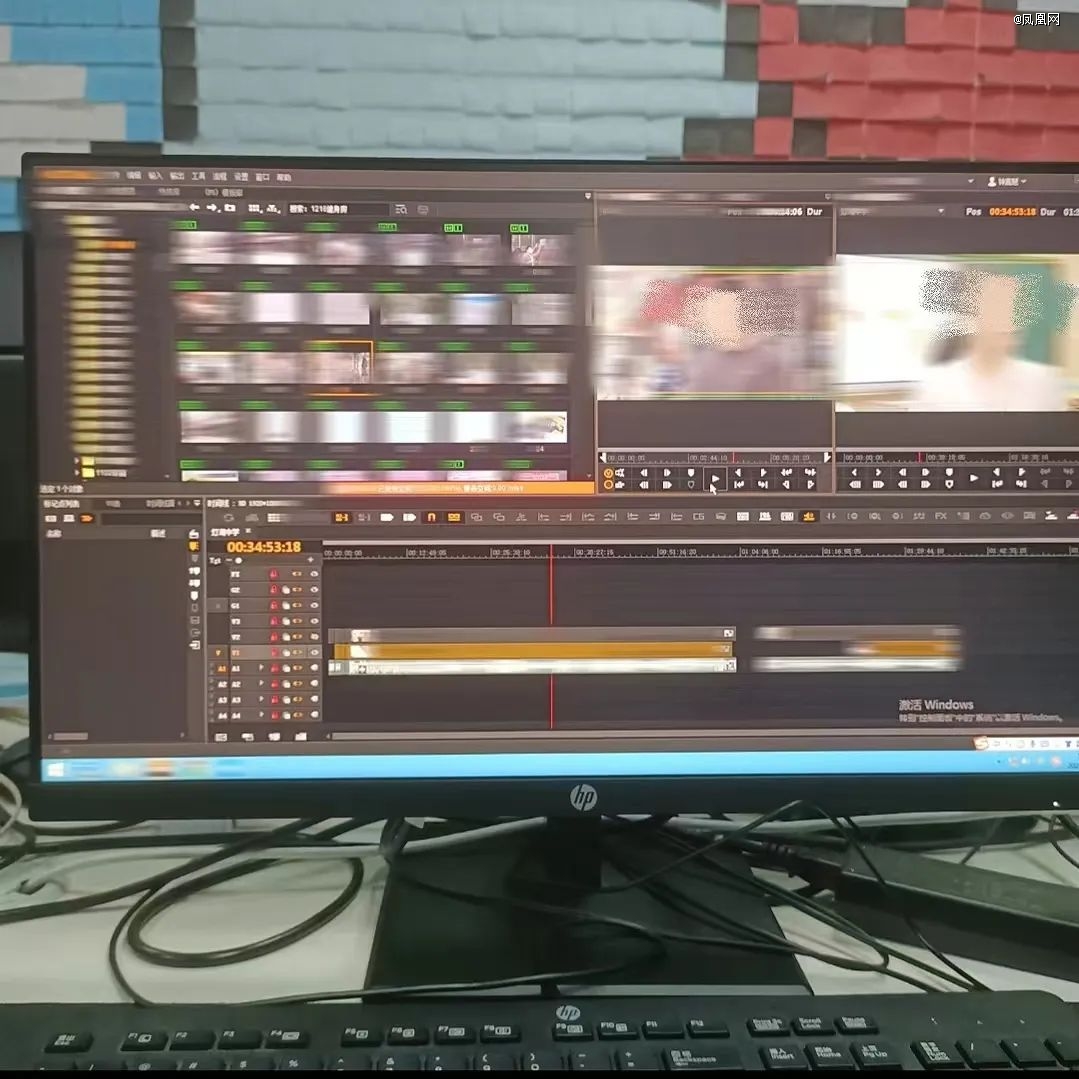 ◎ 陈晨某一份工作的工作照
◎ 陈晨某一份工作的工作照
“在中国的职场,跳槽过和gap过的人等于‘死刑犯’。”梁菲总结。
4年15份工作的经历,也让徐畅成了朋友圈的异类。很多人说,好羡慕你,你的心态真好。也有人问,你家是不是特别有钱?
之前,她会一板一眼地纠正:我家只是普通的工薪家庭,我毕业之后没再管家里要过钱。其实我也想过稳定的生活。一直跳槽,我也很焦虑。
但现在,徐畅已经“不会再争了”。她认为这只是个人选择,多说无用。
毕竟就算亲如父母,也总是因此质疑和否定她。如今,她和父母的沟通仅停留在最基本的生活方面,比如今晚回不回家吃饭,吃什么。他们默契地不提起和工作相关的任何话题,“一说就爆发”。有时在家休息了两三个月,徐畅在自己房间里躺着,父母走进来,欲言又止。压力瞬间冲到她的头顶。
“虽然我对外总是表现得很强势,但我也很敏感,一直很想得到我爸妈的支持,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。”她说道,语气里透着落寞。
面对职场冷眼和亲友的不理解,在和凤凰网的对话中,几乎每个年轻人都谈到了缠绕在他们内心的自我怀疑:“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忍,就我一个人忍不了?”
徐畅试过走上常规的生活轨道,做一个稳定的工作,领一份稳定的收入。在前几个月,她几乎成功了,她以为自己终于蜕变成为一个“情绪稳定”的人。
在那份工作还差一个月就做满一年的时候,她经常觉得手脚发麻,心跳飞快,上医院一查,才知道自己患上严重的焦虑症和抑郁症。医生面容严肃:你太压抑自己的情绪了,必须要改变。她点点头,一出医院就提了辞职。保工作还是保命,她当然选后者。
于是她又回到就业两三个月、休息两三个月的循环里,同时回到生活中的还有父母的不满和讽刺。“就像往我身上扎刀子,”她说,“他们最了解我,所以也最知道怎么让我痛苦。”比如那句她父亲常说的:你住家里都不用交房租,占了大便宜。
对于父母的冷言冷语,徐畅只能忍耐。她考虑过搬出去自己住,但被杭州的经济发展速度打消了念头。她算过一笔账:外面随便租个房就得三千起步,日常开销也要三四千——她平时喜欢逛个酒吧,健个身,现在还在学陶艺。之前她最高拿过月薪一万,“但现在行情不好,多半达不到”。
“我不想放弃现在这样轻松的生活,”她自嘲这是自己的“劣根性”,“如果出去住,我在工作上要吃的苦会多得多,我必须忍到死。”
如今,徐畅只把工作当成一种“赚钱的东西”:“对我来说,可能现在的状态就是最优解。”
其余几位万辞王也是一样,在忍和不忍之间反复横跳。他们都劝过自己“再忍一忍,再多待一段时间”。不过“忍”的意识一旦产生,长则三个月,短则半个月,他们就会发现自己“忍无可忍”。
每到最纠结的时刻,梁菲就会盘算自己的现状:没结婚,没孩子,无房贷,无车贷,父母和自己都身体健康。她想,我有什么必要忍,有什么必要吃这个苦?于是辞职的最后一丝心理压力被卸掉,毕竟,“好工作难找,但月薪三千的遍地都是”。
在一份份工作间辗转腾挪的四年来,徐畅能感觉到自己的变化。
比如她学会了委婉“甩锅”。之前被安排不属于她的工作,她会生硬地直说,这不是我的事情,我不做。现在,她会绕好几个弯,抛出托辞——
这项工作之前一直是其他同事负责,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,交给我做的话,我需要从头学习,对团队而言会浪费比较多的时间,拉低整体的效率。
这在大多数人眼中是日渐“高情商”的表现,但每次在聊天框打出这些话时,徐畅还是会“浑身难受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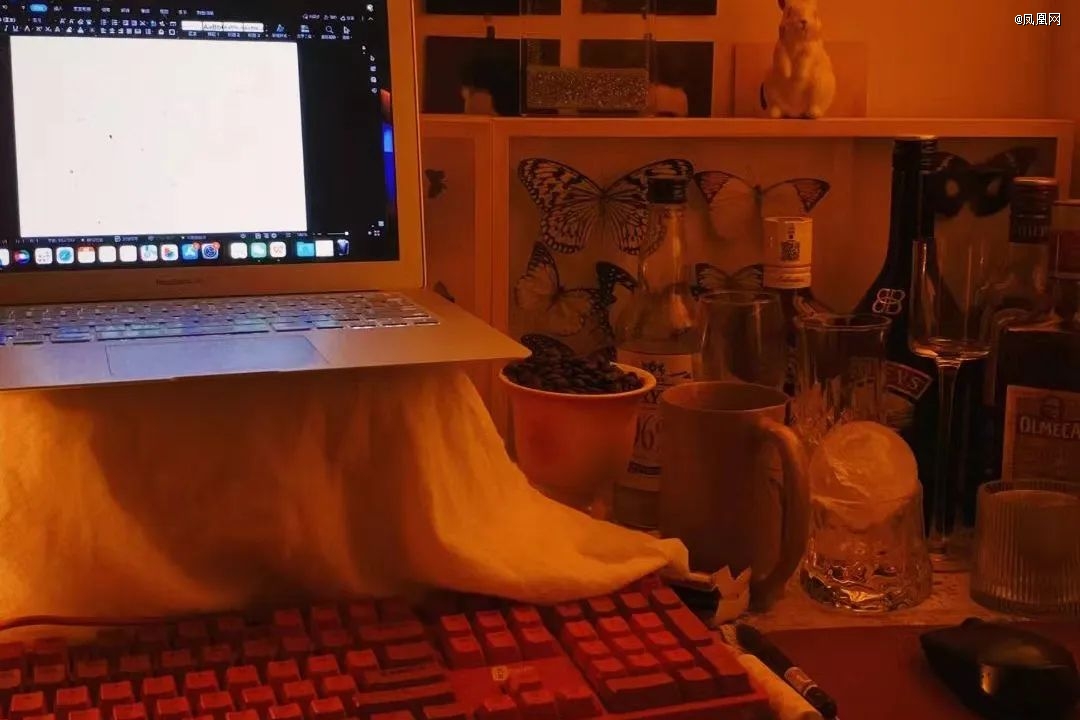
徐畅周末在家加班图
小时候看童话,她常常做“公主梦”;如今再看,她的目光开始为童话里边缘的“小角色”停留:收留白雪公主的七个小矮人是辛勤的矿工,《绿野仙踪》里的铁皮伐木人在劳作时被斧头砍断了四肢、劈开了身体,数不清的侍从和仆人环绕在公主王子身侧。
她不由感慨,同是天涯“打工人”。
从小看的各种文艺作品也教会她,人要善良,要诚实,要追求公平和正义,但进入社会,她在一次又一次的“犯傻”中意识到,这些“美好的品质”,也许反而是一个人成功最大的绊脚石。
夜深人静时,她感到幻灭。但她还不想妥协:
“反正,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”

 Newseeders 合作伙伴
Newseeders 合作伙伴


